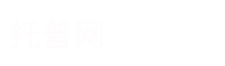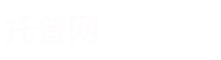高额农村彩礼反映出的社会现状 政府有没有办法调控
近日一则农村彩礼节节攀高的新闻引发关注。“偏远农村多穷汉,讨个媳妇真困难,如今彩礼十几万,其他花费还不算,倾家荡产全抖完,拉下饥荒谁来还?”这是《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中西部某县农村采访时听到的一句顺口溜。
一位特困地区的贫困户年收入只有1万元,但当地的彩礼却十分昂贵,为了娶媳妇举债28万元;有的农村“人情不是债,头顶锅来卖”,赶人情成为不少家庭的主要支出;而看病贵、买房贵、教育负担重等问题更加普遍……
在旧习俗和攀比风气影响下,象征着喜庆幸福的结婚彩礼在一些农村地区反而成了家庭负担。记者采访发现,面对“有利可图”的“彩礼经济”,一些农民将女儿看成集市上“竞价”的“商品”,而为应付高额的结婚彩礼,不少农民家庭债台高筑。
记者近期在中西部部分农村调研发现,随着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步伐加快,教育、住房、医疗、婚丧嫁娶等消费性负担及人情负担有加重迹象,农业现代化过程也暴露出一些制度性交易负担。
这些问题导致一些地方就近城镇化步履维艰,部分农村出现“二次”空心化现象;一些农民收不抵支形成支出型贫困;同时,新经济新业态发展存在一定障碍。

记者近期在湖北、江西、甘肃等地农村调研发现,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农民税费负担锐减,各种强农惠农政策惠及亿万农民。然而,随着农村消费需求的提升,农民在日常生活、教育等方面开支猛增,婚嫁彩礼高企、人情负担沉重,农民消费性的新型负担问题凸显。
部分农村结婚彩礼动辄一二十万元,一些农民不得不举债凑彩礼。在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西坡镇西坡村,贫困户刘雪钗小儿子去年结婚,彩礼花费20万元。这笔彩礼已经超过省城兰州水平。刘雪钗家庭年收入约1万元,加上结婚等开销,目前欠下外债28万元。“彩礼这么高,等大儿子结婚,我还得继续借,把人愁的。”刘雪钗说。
不少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赶人情成为一些家庭的主要支出。“人情不是债,头顶锅来卖。”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码头村村民何宜均说,村里邻居之间随礼要两三百元,远亲至少500元,近亲则要上千元,多的三五千、上万元,即便是贫困户,赶人情一年至少也要上万元。
而村里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风气很盛,家里死个人至少要花五六万元;年前何宜均堂哥去世,一场丧事办下来花了18万多元,收的礼金则超过20万元。
沉重的社会负担使得一些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致贫返贫。甘肃省庆阳市宁县中村镇邓家村贫困户邓拴科有两个儿子。25岁的小儿子在西安的一家电脑学校学技术,每年要开支1.5万元;为给大儿子娶媳妇,老张家总共花掉15万元彩礼钱,至今仍欠下2万元外债,迟迟无法脱贫。
由于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不少农民家里盖着楼房,但为了孩子教育却不得不“蜗居”在城里的一间间陪读房内,或进城买房,无形中构成了新的家庭负担。
今年45岁的高桂女是鄱阳县双港镇人,丈夫在外打工,每年收入只有三四万元,自己陪二女儿在鄱阳县饶州中学读高一。“在这里住很不习惯,既要开销,又不能工作。但看着大家都来陪读,担心自己不来会影响孩子高考发挥。”坐在堆满生活物品的陪读房里,高桂女坦言,家里收入基本只够陪读开销,还有一个儿子马上要读高中,再来陪读负担更重。
一些希望为子女在大城市获得更好教育资源的农村家长开始择校,部分农村逐渐兴起“择校热”。湖北省崇阳县沙坪镇东关村村民刘雄标一家租住在县城的一套破房子里,担心农村小学教学质量不高,他们把两个孩子都送到县城读书,夫妻俩一年只有五六万元的收入,小孩教育支出就要花掉一大半。
还有的农民家庭为让孩子享受到更好教育资源选择在城市买房。
47岁的马振华是江西萍乡湘东区下埠镇虎山村村民,平时主要在村镇安装有线电视赚取收入,一年到头能挣六七万元。马振华在村里有栋自建房,去年7月,他在萍乡中学附近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售价约50万元,前些年攒下的收入都拿来买房了。他说,在农村大家彼此熟门熟户,万一家里有点事邻居也有个照应,进城买房主要是为下一代考虑,“如果家门口就有好学校,家庭负担肯定小很多”。
医疗开支是农村家庭开支的重要部分,一些农民感叹“病不起”。江西省万年县杨芳村村民许保发今年60多岁,妻子早年去世,父子俩相依为命。自认为身体壮实,许保发常年在外从事重体力劳动,基本没有体检过,身患心脏病却不知情。
许保发说:“没检出来还好,万一检查出来怎么办,家里还是拿不出钱来呀。”今年2月,外出打工的他不幸中风,初步治疗花去两三万元。由于家庭收入捉襟见肘,进一步治疗需要花十余万元,不得不暂时搁置。
记者采访了解到,“宁可不知道、也不想体检”的心态在农民家庭里较为普遍,因病致贫也是很多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
此外,当前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城镇化趋势逐渐显现,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节节攀升。55岁的监利县周老嘴镇大李村二组村民吴登喜有记账的习惯,他家里生活开支增长很快,近几年都超过2万元,今年过年办年货就花了1万多元。
吴登喜说:“以前农民都是自给自足,日常开销很小,现在都不怎么养猪种菜了,还老在一块吃吃喝喝,不少人柴米油菜都靠买,这无形中就把开支搞大了。”
出现“二次空心化”现象中西部部分农民面临的这些新负担,势必让一部分人进城难、返乡难,影响就近城镇化进程,制约农村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还会让原本就生活困难的农民难上加难,形成支出型贫困。
中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要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但记者调研发现,不少农民或在家盖起了楼房,或在乡镇或县城买房置业,但由于生活成本渐涨、本地就业机会少,他们不敢返乡、无法进城。
刚在县城宽敞的新房陪两个孩子过完春节,湖北崇阳的“80后”农民工汪庆夫妻俩就返回了上海的工厂,他们原本想在县城找活,由于工资较低不得不放弃。
汪庆说:“孩子慢慢大了,家里房子也装修好了,很想回来工作,但家里的工资比上海每月要低两三千元,自家房贷、小孩读书负担很重,只能在外面再干两年了。”
湖北监利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副局长袁长波说,由于农村社会负担越来越重,很多农民常年在外打工,不敢回家团聚;过个年至少要花1万元,有的人就六七年不回家过年,以规避这些人情负担。
在江西省鄱阳县西分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都建起了两三层的楼房,但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多,房屋空置率高达50%,呈现“二次空心化”趋势,形成资源浪费。“以前大家外出打工是为了盖房子,现在房子盖好了,家里还是留不住人。”今年66岁的鄱阳县西分村村民江明礼说。
制度性交易负担较重,影响农业效益和农村新业态发展。中西部某县一“80后”创业青年两年前从北京返乡从事农村电商,主打黑芝麻系列产品。他说,黑芝麻进入大市场的第一步便是进行产品资质认证,然而自己去跑认证半年都不一定能办下来,而给中介交万把块钱,轻轻松松一个星期就能办下来。
此外,随着农业规模化、现代化逐渐普及,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监利县福娃三丰水稻专业合作社流转了2400多亩、代管1万多亩田地。合作社负责人周振涛说,由于银行贷款难,他不得不找民间借贷,去年光利息就付了10多万元,占到利润的40%。“现在合作社普遍缺资金,利息成本成了很大的负担。”
银行贷款“嫌贫爱富”这一老问题逐渐成为农业新业态发展的“拦路虎”。
今年32岁的肖敏奇是中部某县村民,家里条件比较困难。在外打工十年后,肖敏奇决定返乡创业,从事农村电商,销售村里的大米以及部分土特产。同时,他还去贵州织金县取经,在家种植红托竹荪。
但由于市场研判失误,红托竹荪的销路不畅,去年一年肖敏奇亏损一万多元。创业不顺,加上未成婚,肖敏奇父母也看着着急。过完年后,他重新背起包袱,跟亲戚去云南学手艺。
肖敏奇说,村里一些种植有机水稻、猕猴桃的农户均有机会拿到政府补贴,但他种植竹荪拿不到,有点难以理解。“他们种植规模有几十亩,确实比我规模大,但我们对资金的需求也不一样。”肖敏奇说,本想去银行贷款闯过“创业的第一道关口”,但得到的回复却是“规模太小,又没抵押,贷不到”。
推进供给侧改革基层干部和相关专家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在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要注重进一步减轻农民身上的各种新型负担,提高他们的纯收入和财富积累,真正实现致富奔小康。
首先,应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
袁长波认为,当前农民的需求提升,现有的供给满足不了这些需求,迫使他们花费较大的成本到城市消费。
他建议,大力实施农业、农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资源下沉到乡镇和中心村,送到农民身边,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并逐步引导他们在当地就近完成市民化和城镇化。
其次,应强化基层治理,扎实深入全面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风俗吞噬着农民有限的财富和国家的扶贫资源,在农村社会没有形成有效自治之时,国家择机介入加强引导显得尤为必要。
贺雪峰说,首先要管住基层党员干部,让这部分人不参与;再通过加强文化建设和相关制度建设、订立村规民约等方式,逐渐转变乡村陋习,给不堪重负的广大农民松绑减负。
一些地方已经出台措施,探索移风易俗。江西省文明委日前出台《江西省农村“推动移风易俗 促进乡风文明”行动方案》,明确规定将移风易俗工作列入全省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
再次,应改革创新农业扶持方式,多措并举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成本。
周振涛建议,一方面结合农民需求加强农田水利、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构建大信息平台引导农民合理生产;另一方面着力优化金融、保险等相关服务,结合农业特点推出更多优质低价的金融产品。
同时,加大力度规范基层权力使用,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地,优化创业环境。加强市场监管服务水平,降低农业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农产品入市障碍,让新经济新业态在广大农村蓬勃发展。
娶妻难:一些农村家庭因彩礼债台高筑“偏远农村多穷汉,讨个媳妇真困难,如今彩礼十几万,其他花费还不算,倾家荡产全抖完,拉下饥荒谁来还?”这是《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中西部某县农村采访时听到的一句顺口溜。
在旧习俗和攀比风气影响下,象征着喜庆幸福的结婚彩礼在一些农村地区反而成了家庭负担。记者采访发现,面对“有利可图”的“彩礼经济”,一些农民将女儿看成集市上“竞价”的“商品”,而为应付高额的结婚彩礼,不少农民家庭债台高筑。
专家认为,高额彩礼与过去“重男轻女”引起的男女比例失衡密切相关,不仅让婚姻变了味,也严重影响社会风气。伴随城镇化加速、大量务工人口流动,农村适婚女性数量锐减,高额彩礼在农村仍然存在攀升空间。
记者调研发现,西北地区近年来彩礼价格节节攀高,甘肃庆阳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7850元,而彩礼已经达到了20万元。此外还有“二程”(男方给女方买衣物的钱款)、“三金”等诸多名目繁琐的婚娶习俗,女方还要求买房买车,这样下来一家娶妻成本可高达约60万元。
彩礼价格与贫困程度成正比,一些农村生活水平越低,彩礼负担越重,婚嫁矛盾也越突出。中西部一农村第一书记说,当地彩礼价位与家庭收入紧密挂钩:一等属条件较好者,彩礼20万元以上,家里有房有车;二等属于一般,彩礼10万元上下,这种情况居多;三等是花费五六万元去越南、云南等地买媳妇;四等是家庭财力不够,结不起婚。
越来越重的婚嫁负担,除了致贫返贫,还衍生不少社会问题。由于“娶妻难”凸显,甘肃庆阳甚至出现了“人市”,每年腊月在县城乡镇繁华区,媒人们聚集在这里说媒拉纤,产生了骗婚、“黑媒婆”职业化等乱象。
同时,一些负担沉重的家庭“养老扶幼”问题突出,生活状况令人担忧。自从跟儿媳妇离了婚,儿子就出门打工很少回来,西坡村村民张宗良想给儿子再物色个“二婚”,但彩礼已经涨到了22万元,娶不起。如今,74岁的张宗良成了空巢老人,还抚养着一个留守孙子。走进这个“光棍家庭”,满屋脏乱不堪,桌上剩饭剩菜散发出馊臭。
记者调研发现,多重因素导致农村彩礼高涨。首先,男女比例失衡严重。由于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男多女少较为普遍。江西、湖北等地一些村小组几乎清一色的小伙子,待嫁女青年变得“金贵”。
年逾古稀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码头村村民何宜均年轻时当了近20年村干部。他认为农村传统的“无子意味着绝后”的观念,无形中使得男女比例失调,推高了农村男青年娶妻的难度和成本。村里26岁以上的男光棍就有40多个。
其次,经济基础薄弱。记者发现,但凡是婚嫁歪风盛行地,多属工业薄弱的农业县区,外出务工成为当地农民主要选择,而女性外出后大多不愿再返回农村,进一步加剧女性资源稀缺。
再次,攀比风气成习。“有时候就是个互相攀比的心理,辛辛苦苦养了20多年,如果自己女儿结婚彩礼不如别人家的,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江西省鄱阳县西分村村民江明礼说。
何宜均说,现在村里男青年讨老婆,要有“一座赶时髦的房子、一对年轻的父母、一辆上档次的小轿车”。至于结婚彩礼,少则10来万元,多则二三十万元,另外还流行给女方买金首饰,动辄6金、8金,有一户竟然配了18金。
专家认为,整治“天价彩礼”乱象,单纯通过宣传难以奏效,必须标本兼治,培植婚俗新风的“沃土”。
一是以脱贫促“脱单”。记者回访甘肃省一些曾经的“光棍村”发现,近几年当地通过培育产业、发展农村企业,村民的致富水平提升,光棍的数量随之锐减,比脱贫还难的“脱单”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张建君认为,农村形成相应规模的产业合作体,容纳青年农民工就近就业、增加收入,有望从根本上铲除旧俗习气滋生的土壤。
二是增强民间中介“话语权”。近年来,江西省寻乌县一些农村通过民情理事会等方式探索移风易俗,治理天价彩礼、赌博等陋习,取得了一些成效。江西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马雪松建议,不妨加大力度探索建立类似的村民组织,遏制婚俗陋习,引导树立婚嫁新风。
三是平衡农村性别比例。专家建议,各级卫计、司法、公安、教育等部门加强协作、对涉及胎儿性别鉴定、人流、采血送境外鉴定胎儿等违法广告进行集中整治,严格B超仪器管理。
四是政府主动“牵线搭桥”。组织农村青年相亲会、鹊桥会,成立乡镇婚介所,举办集体婚礼,为他们创造婚恋渠道和平台。

推荐文章
Recommend article
热门文章
HOT NEWS